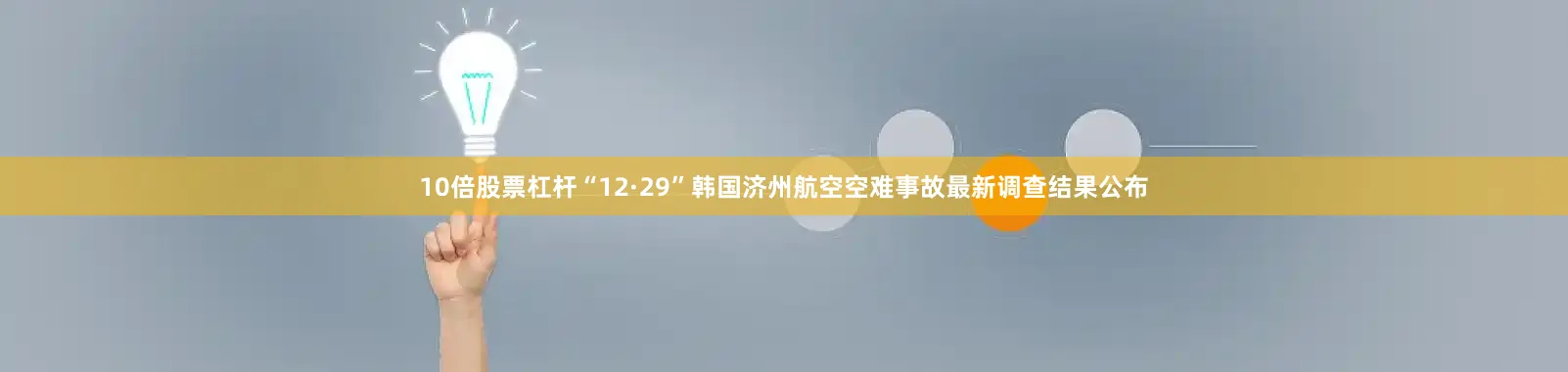在中环午餐吃什么是令上班族头疼的问题,位于中环士丹利街的一整列铁皮摊档,在高楼林立、寸土寸金的金融商圈里,可说是相当独特的存在。其中有50年历史的“盛记”是人气最旺的摊档,还上过“舌尖上的中国”。
盛记的腰果珍肝好吃,鸡肝、鸡胗、芹菜与腰果的组合算是少见,火候炒得恰到好处,芹菜保有水份不带生味,腰果口感跟香气搭配,让食客忽略了环境的简陋。
香港在1847年设立的小贩牌照成为大牌档的缘起。1921年,首个持牌大牌档诞生。当时将小贩分成固定小贩牌照和流动小贩牌照两种牌照,前者称“大牌”,后者称“小牌”,统称熟食档。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,香港将大牌和经营熟食档的牌照合二为一,使街头熟食摊贩成为“大牌档”。为避免街头出现大量未经批准摆卖熟食的摊档,政府规定持牌的固定熟食档需要展示牌照,相比其他路边摊,固定熟食档的牌照是注有持牌人及档位资料的一张大纸,这个牌照需要裱装起来及挂在档位的显眼位置,因此这类街头熟食档被称为“大牌档”。
还有一个说法是,由于早年香港的大牌档供食客使用的座位是用木造的长凳,食客围着饭桌并排就坐,而且“牌”和“排”是同音字,因此“大排档”也成为普遍的写法。
大牌档的外观近似一个摆放在街头的巨型铁皮箱,因为铁皮容易生锈,所以大牌档都涂上绿色的油漆防止锈蚀。选用绿色倒不是法律规定,而是因为绿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最便宜的油漆颜色之一。绿色在军事上具有保护色的作用,成为英美盟军在坦克和军车上的主要涂装颜色,等战争打完了,绿色和具有相同用途的啡色、灰色和黑色的油漆,便成为了有大量库存的战争剩余物资,所以这四种颜色的油漆售价比其他色彩低廉,而绿色又较啡色、灰色和黑色鲜艳,因此成为便宜又实用的油漆颜色之首选。万物都可以在经济学上找到缘由。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,政府以整顿市容为由对大牌档的经营逐渐施加限制,部分大牌档需要迁入熟食中心,如果不愿意搬迁可交还牌照,并领取指定金额的补偿。政府于1972年停止发放经营大牌档所需的“固定摊位(熟食或小食)小贩牌照”,自此香港再没有持有这种牌照的新大牌档开业。
中环、上环及湾仔一带,都是香港人口及商贸活动的集中地,遂成为大牌档的发祥地。这些早期的香港市区在踏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渐次进行旧区重建,不少大牌档因土地需要收回发展,加上早年获发牌的持牌人已经年迈,政府又不允许子女继承牌照,唯有将牌照交还政府。亦有部分是被政府要求收回,其间很多大牌档因此结业。
到了2005年,整个香港仅剩下28家持有“大牌档”牌照的食店,政府于2009年宣布大牌档活化计划,为中环的10个大牌档进行排污改善工程,并研究为档位接驳煤气。
其实, 大牌档文化远不止于市井烟火的表象,而是城市空间设计、文化符号和微型经济形态的综合体现。战后物资短缺,基层民众“手停口停”,小贩独创出碗仔翅、鸡蛋仔。大牌档有不少闻名的菜式,例如豉椒炒蚬、椒盐濑尿虾、避风塘炒蟹和干炒牛河,深受不同阶层的客人喜爱。他们展示的草根精神和美食文化,是香港人灵活务实的体现。
今年大火的电影《水饺皇后》,臧姑娘从木头车摆卖到创立“湾仔码头”品牌,其励志故事创出4个多亿票房。观众们不仅在生活中吃过湾仔码头的水饺,也在影院里回顾了昔日香港基层自强的故事。大牌档是文化创意的孵化器,更是维系社区情感的纽带。这份文化与精神价值,正是香港需要珍视与传承的资产。
放眼全球,小贩文化并不少见。新加坡餐饮从业人员超过12万,而国家环境局下设的小贩署和卫生署仅有200多名食品卫生稽查员,负责执法检查。新加坡更将小贩中心成功申遗,正因其促进了社区互动、凝聚多元族群的社会价值。当地政府开放牌照市场,允许牌照转让与重新分配,并推行培训计划引进“新血”,避免行业断层。
德国纽伦堡圣诞市集将美食、手工艺与表演艺术融为一体,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,用热烈的节日氛围带动相关产业。逛集市给亲朋好友选购礼物成为人们难忘的快乐记忆。相比之下,香港长期将公共空间高度规范化,市民参与规划的权利被压缩,摆摊设点更被视为“秩序破坏者”。摊贩问题的症结,在于公共空间的治理逻辑。
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让每一个人都成了情感(心理)上的早产儿。一座城市的灵魂,不在摩天大楼的光鲜外表,而在街角巷尾的人情温度。香港的牌档政策,若能超越“规范整治”的单一视角,看到更高层的精神和文化意义,将有望同步提升其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可持续的经济效益。
本版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
股票配资开户,炒股杠杆怎么开户,大华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